人类的危机 演讲 人类的危机:从荒诞到反抗
下面是好好范文网小编收集整理的人类的危机 演讲 人类的危机:从荒诞到反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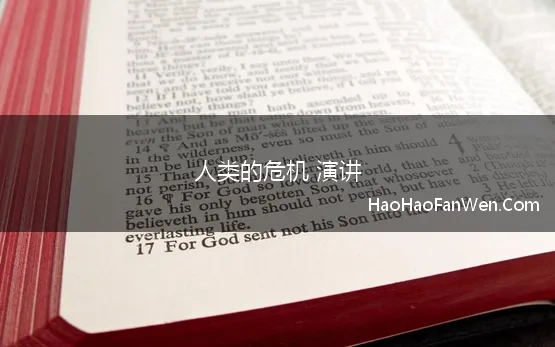
按:1946年3月25日,阿尔贝·加缪抵达了纽约,在McMillin剧院进行了名为《人类的危机》的演讲。这场演讲正如其名,毫不留情地指出人类正面临的危机:施害者的残忍、旁观者的残忍。但加缪不满足于只指出问题,还为之开出药方:反抗。
这场演讲意义非凡。70年后的2016年,为纪念加缪到访七十周年,纽约组织了一系列阅读、表演和讨论活动,为“加缪月”。活动期间,《洛杉矶书评》的历史编辑、《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的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受邀与《纽约客》撰稿人Adam Gopnik举行对话,讨论加缪的人生及其作品在21世纪的位置。今天推送的,即是这场对话的节选。罗伯特·泽拉塔斯基再次阐释了加缪的演讲《人类的危机》,也再次阐释了加缪。
人类的危机:从荒诞到反抗
文 /[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
译 /李孟林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辑所加
在名为《人类的危机》演讲中,加缪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艰难的任务。面对挤满剧院的美国年轻人,他想要讲述那些肆虐欧洲的事件的特点和后果,而这些事件几乎没有触动他面前的听众。“我这一代的男男女女,”他如此开头:
“出生于一战爆发前或战时,青少年时期遇到了大萧条,20来岁时希特勒掌权登台。我们还遇上了西班牙内战、慕尼黑事件,以及战败、占领和抵抗接连发生的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时我们接受的教育终于完成。”
这样的成长经历,加缪讽刺地总结到,塑造了“有意思的一代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荒谬性,他们那一代人必须找到抵抗和反叛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哪儿能找到呢?无论宗教还是政治都不能提供指引,而传统道德则是“骇人的虚伪”。在一个被大屠杀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大陆上,在一个遍布虚无主义的世界中,加缪这一代人被抛入了最恐怖的矛盾之中。“我们厌恶战争和暴力,然而我们必须接受这两者。”简短来说,他们遭遇了人类的危机。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这一点,加缪举了几个生活在纳粹占领下的事例。在欧洲某处一座盖世太保的大楼里,看门人走进一间公寓时,两个男人因为涉嫌从事抵抗活动而被殴打,并被拷走。当其中一人请求帮助时,她带着骄傲回答:“我从来不管楼里住户的闲事。”还有一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人,他是加缪的抵抗运动同志。此人被带到一间党卫军军官的房间,前一天他的耳朵就是在这里被割掉的。那名监督了此项暴行的军官充满同情地问到:“告诉我,你的耳朵怎么样了?”最后,还有一位希腊母亲,她得知抓走自己三个儿子的德国士兵将要枪杀他们。她请求军官放过自己的儿子,这个军官提供了一项妥协:可以放过一个儿子,但是母亲必须挑选放走哪一个。她选了大儿子,因而将另外两个儿子送上了死路。
加缪告诉他的听众,他选取这些故事并非要惊吓他们,而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残忍世界的果实: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仅施加残忍,而且这种残忍在行凶者身上除了冷漠以外激不起任何情感,而目击者则接受了残忍。当我们面对一个被杀害或被折磨的人类同胞时,我们的反应却不是恐怖或愤怒;当我们觉得精心向他人施加痛苦,并不比每天排队等候食物供给更令人烦恼时;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不会仅仅因为希特勒的灭亡就会变得更好。加缪扫视着大厅,他宣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寻找这些骇人邪恶的原因,这些邪恶仍然在撕咬着欧洲的灵魂。”
加缪对我们的处境做出了黑暗的诊断,但他提供的处方也几乎同样地黑暗。虽然没有充满希望的理由,但这却不是绝望的理由。他宣称,我们可以解决这场危机,只要有“我们仍然掌握的那些价值——简单说,对我们生活的荒诞性的意识。”这并不是形而上学上的宏大言论,或者那种在法语中听起来比在英语中更好听的说辞。加缪所做的是援引那些塑造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的世界的哲学和道德主题。
尽管两本书当时都没有翻译成英文,听众中很多人肯定听说过后一本书的开头那段话。“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决定生命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游戏;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发现在自己处在“一个突然间剥离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然而仍然坚持寻找意义时,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加缪想知道,当我们“对明确的非理性且急切的渴望”遭遇到“世界不可理喻的沉默”时,自杀是否是唯一合理的回应。他质问道,有可能“过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但是听众可能并不知道,加缪自那以后已经超越了早期作品。尽管这些书自1942年出版后大获好评,但是加缪认识到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默尔索(《局外人》的主人公)和西西弗斯单打独斗的反抗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到了再次衡量荒诞之限度的时候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发问,当一个思想家宣称:“此前我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现在我要重新开始“时,这个世界该对此做何种理解?让他宽慰的是,他认识到这并不重要。
这并不是加缪现在所把握到的全部。他认为荒诞“无法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诊断视为不幸——我们不应该像默尔索或西西弗斯那样仅仅关注自己——而是应该关注他人。说到底,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悲哀与伟大: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爱的对象,”他在日记里说到。“荒诞是君王,但是爱将我们从它的手里拯救出来。”爱将我们从荒诞中解救出来。
四年之后,当他登上McMillin剧院的舞台时,加缪已经将荒诞留在身后。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反抗。他那时已经完成了《鼠疫》——于随后一年出版——而且已经开始写作《反抗者》。他在讲座中勾画了后来这本书的主题。他讲到,在一个缺乏意义的世界,太多人觉得成功的人就是正确的,而正确与否是靠成功来衡量的。对于那些抵制这种看法的人,对于那些不愿意生活在施虐者和受害人的世界之中的人来说,不论信仰还是哲学都无法提供资源。唯一的辩护资源来自于“反抗这一行动本身。”加缪总结道,我们为之抗争的“并非仅仅为我们所有,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仍然拥有意义。”
但是这种关于意义的主张,在美国又能意味什么呢?加缪说,在这个快乐的国度里,他的听众看不到“或者只能模糊地看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需要知道有人“曾经在数年里目睹了这些邪恶,仍然在他们的身体里感受到、在他们深爱之人的脸上看到这种邪恶。”但是这些反抗者,加缪随后澄清,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不仅拒绝了形而上学的荒诞,也拒绝了政治上的荒诞:国家坚持要给施加于公民身上的毫无道理的痛苦以某种意义。这些反抗者不仅对无言的宇宙说“不”,也向不正义的统治者说“不”。他们并不尝试征服,而仅仅去是直面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和那些否认他们人性的人。
然而,最关键的是,反抗者为自己设置了界限。反抗是一种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行为。它是平衡,而不是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它要求既要看到自己的人性也要看到他人的人性。正如荒诞绝不意味着绝望,更不意味着虚无主义一样,暴君的行为也绝不意味着另一个人可以以暴虐的方式回击。反抗者拥抱”界限的哲学”,并不否认他的主人也是人类同胞的一员,他仅仅否认对方是自己的主人;他抵制那种对从前的压迫者实行非人化对待的强烈诱惑。总的来说,反抗者“渴求的是相对,并且设定了界限,人类的共同体就在这个界限上建立了起来”。
在他演讲的最后,加缪邀请听众也加入正在高涨的反抗浪潮。“对于正在听我们讲话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说道,这一代欧洲反抗者“尊重那赋予你们活力的人性,还有反映在你们脸上的自由和幸福。他们希望你们,以及所有怀着善意的人们:能够忠诚地参与到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话中。”如果70年前这些文字在美国留下了一些印记,今天它们还能吗?加缪会对我们今天荒诞的政治气候说些什么呢,如果他真有什么要说的话?当然,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把握的是,今天的美国人会像1946年一样让他困惑。
加缪发表过一篇名为《纽约的雨》的短文,是根据美国之行而写的。在文中他坦承,尽管在纽约呆了数周时间,他"仍然对纽约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处于一群疯子之中,还是处于全世界最理性的人之中;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是否像所有美国人声称的那样容易,还是说如它有时候看起来那样的空虚;……不知道这有没有任何意义: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团在4个舞台上同时上演10个节目,这样你能同时对所有节目产生兴趣但又一个也看不成。"
加缪对美国人的困惑也变成了我们的困惑,而他70年前所做的观察到今天仍然一样尖锐。我们政治马戏团的40个舞台,其中混杂着疯狂和理性;我们在媒体上轻易地谈论残忍,分析里空无一物:所有这一切都响应着McMillin剧院那一晚的演讲。这种困惑不会很快结束,但是正如加缪对听众所言,我们必须开始衡量我们的言辞。他宣称,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容许自己思考某些思想时,我们会杀害数百万人类。”
▼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 著
王兴亮 译 贾晓光 校
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
201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