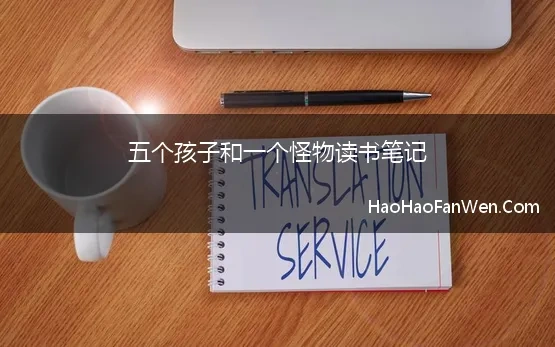风雨文谈是论文集吗(《风雨谈》读书笔记)
下面是好好范文网小编收集整理的风雨文谈是论文集吗(《风雨谈》读书笔记),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平平淡淡的作业尔尔
一.出版情况
上文中“总的题目”说得较为含糊,岳麓书社版《风雨谈》的《重版说明》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录——“‘风雨谈’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五月周作人在《宇宙风》半月刊所开随笔专栏名。”《重版说明》中甚至还录存了《宇宙风·风雨谈》专栏所发的十篇文章及其部分原题:“依序为《小引》、《<游山日记>》、《<记海错>》、《<钝吟杂录>》(原题《宋人的文章思想》)、《陶筠庵论竟陵派》、《<窦存>》、《<逸语>与<论语>》、《郁冈斋<笔塵>》(原题《谈诗文》)、《<蒿庵闲话>》(原题《文人之行》)、《<鸦片事略>》(原题《谈鸦片》),全都收入了本集。集中其他的文章,便是发表在《北平晨报》《益世报》《自由评论》等其他报刊上的了。”
但是翻一翻《周作人年谱》就可以发觉上面的原题标注得并不完全,如《<逸语>与<论语>》的原题是《逸语与论语并说到孔子的益友》,收题是改为《论语与逸语》,后面是如何竟变成了《<逸语>与<论语>》,尚未可知,如果是今之编者根据文章的叙述顺序先讲《逸语》后讲《论语》而改的话,似有点自作主张之嫌;《书法精言》的原题是《王锡侯书法精言》。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北平晨报》、《益世报》、《自由评论》”之外,包含在“等其他报刊”之中的还有《大公报·文艺》[1]、《国闻周报》[2]、《青年界》[3]、《逸经》[4]、《青年界》[5],岳麓书社的编者颇为偷懒,这点小活都不愿意做。
二.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是一个很难聊的大话题,困扰之余,我也在翻阅《周作人年谱》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1935年11月以至1936年5月这段时间里,编者在开头1935年、1936年的总纲下归纳了每月发生的大事概要,但是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和下面编者按照12个月逐日记录的周作人生活(主要以交往和写作为主)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如果我们将前者理解为政治背景与时事环境,将后者理解为周作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两者竟然如此剧烈地分离:前者展现出来的是箭在弦上的十万火急与时代动荡的风云剧变,而后者始终冲淡闲适且波澜不起。
作家,作为个人,在历史沉浮之中保持着他之于时代的精神距离,这种保持往往是有意的主观选择与所迫的客观生活双重影响下的结果,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主观选择是不同的:有的亲切,誓要同呼吸共命运,有的疏远,不愿管门前瓦上霜;但是无论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时代总是左右局限着这种自由,局限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与个人紧密贴合的现实生活,比如我便是通过无法再自由出门按时返校而切身感受到今年的疫情的,我们都是通过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来体贴宏观时代的那些大叙事的,时代也是通过无数个细微的现实生活片段来施加它对于个人的影响。很多时候,个人的有一种悲哀便在于无法选择置身于时代之外,我指的便是四十年代的周作人。
言归正传,1935年的1月,红军占领遵义,确立了毛领导的中央;2月,日本关东军阴谋制造华北地区的“自治运动”,实现吞并华北的目的;8月,中国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主张停止抗日,一致对外;12月,“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1936年4月,周张在延安会谈……这些震撼时代的大事都跟周作人的《风雨谈》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将其统统关在门外尔后在“自己的园地”里“闭户读书”的[6],唯一能扯得上联系的恐怕就是9月的那条记录“《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后改为旬刊,林语堂主编”,联系的原因在“出版情况”中也说得很明白了。
然而,与《风雨谈》的写作更有关联的应该是周作人的阅读书籍与私人生活,但是《周作人年谱》中可见寥寥(以此要求年谱,似乎也有点过分,只是既然以周氏书写的历程来倒编年谱,又少有周氏生活所历迹,不如改称“周作人书谱”较为恰当),抄录几则如下:
“本年[7]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为歌谣研究会委员。……
1936年2月 参加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议决:(1)恢复《歌谣》周刊[8],请徐芳、李素英编辑,从第98期起,称为第2卷第1期。(2)编辑‘新国风’丛书,专收各地歌谣专集,由北大出版组印行。(3)发起组织一个风谣学会……”
这条记录大抵与《<绍兴儿歌述略>》有关,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六年四月来到北京大学,不久歌谣研究会成立,我也在内,我所有的也只是这册稿子。今年歌谣整理会复兴,我又把稿子拿出来,这回或有出版的希望。”《绍兴儿歌述略》可能是打算要收在“新国风”丛书里的,这篇《<绍兴儿童述略>》也正是载于第2卷第3期,应该是歌谣研究会给周作人出的题目。
“1936年27日 复陶亢德信,收1943年4月《古今》半月刊第20、21期合刊陶亢德《知堂与鼎堂》文。时陶亢德正与郭沫若通信争论‘幽默小品文’事,周作人认为:‘互讦恐不合宜,虑多为小人们窃笑也’。”
我的这一个发现非常有趣,《日本的落语》这篇文章写于“廿五年上丁”,《周作人年谱》的编者可能懒得考证这到底是哪一日于是把这篇文章略去不写了,上丁也就是农历初四,换算到公历是27日,也就是给陶亢德写信的那一天,这是有趣的巧合,以此来看《日本的落语》中“中国文学美术中滑稽的分子似乎太是缺乏”,便觉得两处意思是可以互文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本来就是同一天写就的,从中亦可见周氏的态度大概是不与人争,而自作微叹遗憾之慨。
三.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无非是用自己的话说说自己读过的文献罢,然而涉及《风雨谈》的研究论文很少,几乎没有——彭雪英《周作人与晚明小品关系论》多次引到《风雨谈》中《<梅花草堂笔谈>等》来论述三十年代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喜爱,又以《陶筠庵论竟陵派》、《郁冈斋<笔塵>》两篇来阐述周作人对晚明文学的维护与向世人的介绍;贾雅雯《周作人散文“文抄”体式研究——以其30年代散文为例》则将《风雨谈》与三十年代周氏的其他著作一起作为解读阐释“文抄体”的材料……又看了几篇,其大意还是类似,总离不开“文抄”、“晚明小品”等老生常谈的诸调,很没有意思的,其实《风雨谈》是有其特殊性的,它很可以作为专门研究的主体,可以说它是周作人自编集中唯一一个题目关乎《诗经》的集子,很适合作为周作人的诗经研究的一个引子,但无论是《风雨谈》还是周作人的诗经研究都没有人做就是了,挺遗憾的。
四.涉及议题
《风雨谈》涉及的议题颇为丰富驳杂,正如周氏的兴趣一样,其中关于文人书话与文学观点的部分,我在之前写的《周作人的意气与私心——趣话<风雨谈>中关于文人的爱憎》一文中已经分门别类地列举地很详细了,有兴趣自然不妨去看,如今便来聊聊其他剩下的话题。
《老年》谈及的是老年生活,周氏是将其放在“人有生老病苦”的大话题下来谈的;《三部乡土诗》涉及“同乡人的著作”,与之意思相似的是《<绍兴儿歌述略>序》,介绍了绍兴儿歌,于之上下四旁言之;与日本相关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的落语》、日本管窥之三,“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周氏的态度是寂寞,所见亦是丰富驳杂;记录名物者,有《谈海错》、《关于纸》、《螟蛉与萤火》、《买墨小记》、《鸦片事略》,博物学知识与古书考证兼之;《北平的春天》与《旧日记抄》比较特殊,文抄的部分有周氏自己的文字,或为诗或为日记,所以往往会在其后作笑谑的自嘲抑或谦深的默想,总之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文学的未来》与《本色》所谈接近纯文学,颇空灵巧妙,所持亦总有独到。
据康老师说大抵是三千字来着,如今已然是超了一点,那便写到这里就此作罢了,兴致恰好也乏了,不妨以一个谜题结尾——如何用四个字来概括三十年周作人的文风与个性?
我取“然而不然”;此话既是周氏口癖,又和他的个性文风契合得切巧,大概不会有比这更妙的答案了吧。
[1] 收《三部乡土诗》,载于《大公报·文艺》第70期
[2] 收《日本管窥之三》,载于1936年1月1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收《安徒生的四篇童话》,载于2月10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3] 收《螟蛉与萤火》,载3月《青年界》第9卷第3期
[4] 收《<日本杂事诗>》,载于4月5日《逸经》半月刊第3期;收《王锡侯书法精言》,载于5月5日《逸经》第5期
[5] 收《读戒律》,载于9月《青年界》第10卷第2期
[6] 就文学表现的题裁与现实生活、历史时事之关系而言,周作人和黑塞挺像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生来便如此吧,或者后天如此,也未可知。
[7] 这里指的是1935年
[8] 《周作人年谱》中此处有误,其名便是《歌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