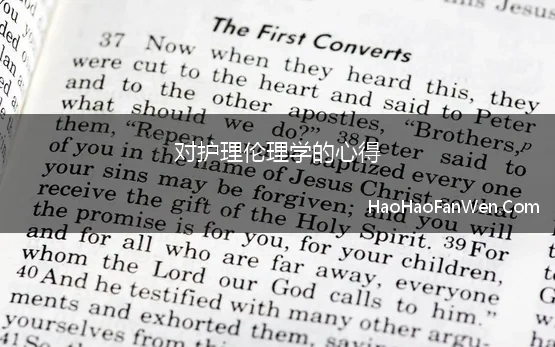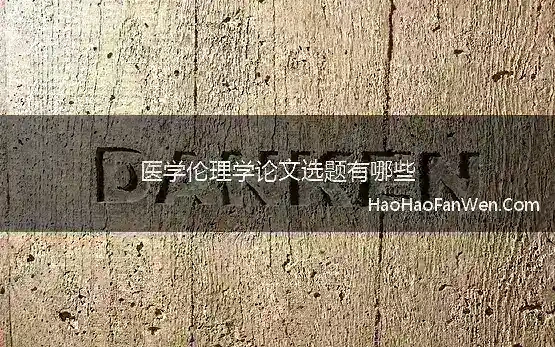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
下面是好好范文网小编收集整理的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提 要】本文的基本课题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义论?正义论与伦理学之间是什么关系?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性分析,本文指出其因为缺乏对规范与制度的区分而导致的正义论之论域的狭隘、因为缺乏对规范与原则的区分而导致的正义原则的空白、其仅仅是一种“现代社会正义论”而非普适的一般正义论的性质、其“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的偏狭等问题,最后提出“一般正义论乃是基础伦理学”的新观点。
【关键词】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罗尔斯;伦理学;基础伦理学
本文的基本课题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义论?正义论与伦理学之间是什么关系?鉴于国内现有的正义论研究主要是由美国学者罗尔斯(J. Rawls)的《正义论》所触发的,该正义论在西方正义论中是具有典范性的,我们这里主要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来讨论“什么是正义论”的问题。
这里须预先说明的是:罗尔斯正义论所传达的那些价值观,并不是我们一概反对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下,诸如“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观也是我们所主张的。我们在这里要与罗尔斯展开商榷的,不是这些价值观在现代生活方式下是不是可取的问题,而是这些价值观在一般正义论的建构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的问题,例如“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可以充当正义原则或其前提的问题。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中国正义论之间具有一些基本的可对应性,如正义论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有: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这在中国正义论中就是“义利关系”问题;建构制度规范的根据乃是正义原则,这在中国正义论中就是“义→礼”关系问题;正义意味着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当性、适宜性,这在中国正义论中就是“义”所蕴涵的正当性原则(正)、适宜性原则(宜);如何建立正义原则、其与仁爱情感之间是何关系的问题,这在中国正义论中就是“仁→义”关系问题;等等。但是,尽管如此,中、西正义论之间却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异(即便在上述对应之点上也是存在着重大的非等同性)[①],这里择要讨论与这篇导论有关的以下几点:
一、正义论的论域:社会规范
正义论的核心课题当然是正义原则、即“义”的确立;而之所以要确立正义原则,则是要为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即“礼”的制定竖立一种价值尺度,亦即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②])。显然,如果我们确立了一种正义原则,那么这种价值尺度应当是适用于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社会的主要制度、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说:
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这样,对于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护、竞争市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社会制度的实例。把这些因素合为一体的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③]
这就是说,罗尔斯所关心的只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是“主要制度”。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二:
1、从范围看,罗尔斯所关注的当然是正义论的重要论域,但却并不是正义论的全部论域。而中国正义论之所谓“礼”,乃是包含了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例如一部《周礼》,就是涵盖了全部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④] 我们认为,关于一般正义论所关注的东西,我们只须提到“制度规范”(norm-institution)(本文对于“规范及其制度”[norm and its institution]的省称)即可,这样一来,举凡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家庭规范、思想规范等等一切规范及其制度皆在其中,这样的正义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正义论来说,这个范围甚至还应该更一步扩展。罗尔斯承认道:“作为公平的正义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契约论。…… 它看来只包括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不考虑我们在对待动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方面的行为方式。”[⑤] 这起比中国正义论的外延来要狭隘得多,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涵盖了人与物的关系,乃是一种“万物一体之仁”的视域。例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⑥])孟子在这里给出了中国正义论的外延的一种扩展序列,即:亲人→他人→它物。在今天这个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正义论外延的这种扩展是必要的、紧迫的。对于中国正义论来说,所谓“社会”远不仅仅意味着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义与否,也远不仅仅是人自己的问题。
2、从层面看,罗尔斯所关注的只是“制度”层面。但制度不过是社会规范的制度化、或者说是制度化的社会规范。罗尔斯缺乏一种必要的区分:制度与规范的区分。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范,诸如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家庭规范、行业规范等广义的伦理规范,其中有一些规范是可以制度化的,但有一些规范却是无法制度化的。例如并不存在所谓“道德制度”,因为道德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并没有什么实体化、刚性化的制度设置。真正全面的正义论,所关注的乃是、也仅仅是所有一切社会规范;解决了规范的正义问题,制度的正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正义论的主题:正义原则
罗尔斯明确提出: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某种“原初契约”,这种原初契约被用以“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契约”。[⑦] 所谓“进一步的契约”,也就是一个社会所要建立的制度规范。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其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并未提出任何正义原则;用中国正义论的话语讲,罗尔斯所论的只是“礼”、没有“义”。
我们预料,这个判断可能会遭到罗尔斯研究专家的强烈反对。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根据是:不论是“原初契约”、还是“进一步的契约”,都是契约;换句话说,它们都属于规范的范畴,而非规范赖以建立的更为先行的原则。所谓契约,就是人们之间所达成的规范,亦即人们在某种事情上所达成的规则;而要达成这种规范、规则,人们需要某种更为先行的价值原则,而且这种原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规范或契约。这种原则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
显然,罗尔斯缺乏另一种重要的明确区分,即“原则”(principle)与“规范”(norm)的区分。[⑧] 实际上,规范总是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其问题结构是:人们为什么要建构或选择如此这般的一种规范?这种建构或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就是原则,它表现为某种价值判断,而充当对规范及其制度进行价值评判的尺度。显然,原则和规范不是一回事,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我们切不可以将规范误认为原则。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总是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亦即孟子揭示的这样一种奠基关系:义(正义原则)→ 礼(社会规范)。[⑨] 人们总是根据某种原则(义)来建立或选择某种规范(礼)。按儒家的看法,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世”的。
第一个原则是:
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这里所谓“自由体系”作为一种“体系”(制度),显然就是某种社会规范体系(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规范),却在这里充当了一种先于并且据以给出正义原则的、既定的前提条件;每个人对于这种规范体系的平等权利,这种权利规定显然也是一种规范建构,而且它本身就是属于那个规范体系的,因而对于那个既定的体系来说是无须作为一条原则来加以重申的。我们不难发现,罗尔斯讨论正义原则问题时的前提,就是某种“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显然不是那个应当先于任何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却在这里充当了“正义原则”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原则是: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这种“安排”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其基础就是上述第一个原则所确认的那个社会规范体系: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从属于那个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见下文的第一个优先规则);机会公平平等的制度安排本身也是属于那个基本自由体系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本是“机会公平平等的”制度安排的题中固有之义,因而也无须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来加以强调。
罗尔斯还补充性地提出了两个“优先规则”。第一个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性)是:
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况:(1)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2)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
第二个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是:
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有两种情况:(1)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2)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11]
这些“优先规则”既称之为“规则”,就已经是规范的范畴了;换句话说,它们同样不是先于任何规则、规范、制度的原则本身。
罗尔斯的整部《正义论》,就是试图详尽地论证这些“原则”及其“规则”。这些“原初契约”或“最初安排”[12],其实根本就不是正义“原则”,而是一些社会规范,它们本来是应该由正义原则来奠基的;它们甚至不仅仅是规范,而且已经是一种制度设计,这就正如罗尔斯自己所说:“两个正义原则自身中已经孕育了某种社会制度的理想”;例如“差别原则不仅假定着别的一些原则的实行,而且也以某种社会制度理论为前提”;“因此我们需要毫不犹豫地在决定正义原则的选择时预先假定某种社会制度的理论”[13]。用儒家的话来说,罗尔斯在这里所陈述的都是“礼”,而非为之奠基的“义”。
既然这里陈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社会规范、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在罗尔斯这里,为所谓“正义的两个原则”(实则是两条基本的社会规范)奠基的那种更为先行的、真正的正义原则究竟是什么?存在着三种可能:
第一、在第29节里,罗尔斯提出了一些“正义原则的主要根据”,诸如“承诺的强度”、“公开性的条件和对契约的限制条件”等。但我们不必详细讨论这些根据,因为罗尔斯自己说:这些都是作为“论据”、而不是作为原则来讨论的;而且它们“依赖下述事实:对于一个将确实有效的契约来说,各方必须能够在所有有关的和可预见的环境里尊重它”;“这样,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比前面的讨论显得更为依赖于契约概念”。[14] 这就是说,这些“根据”仍然未能超出契约、规范、制度的范畴,即仍不能是真正的正义原则。
第二、所谓“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鉴于“正义的两个原则”是直接从“原初状态”中推出的,那么这种“原初状态”似乎就可以视为对“原初契约”的奠基。但是,以下几点否定了这种可能:(1)罗尔斯本人很明确:原初状态作为一种“状态”不是正义原则,而不过是借以推出正义原则的条件。(2)罗尔斯说:“我所说的原初状态的概念,是一种用于正义论目的的、有关这种最初选择状态的最可取的哲学解释”;“我强调这种原初状态是纯粹假设的”;例如需要“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假设。[15] 然而就方法论而言,这种由“纯粹假设”出发来推出正义原则的做法是可以质疑的。中国正义论认为,正义原则的确立并不是基于一些哲学假设,而是源于生活的实情和作为一种生活感悟的正义感。(3)罗尔斯继续道:“但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何为最可取的解释呢?”这就需要 “使正义的理论与合理选择的理论联系起来”。[16] 上述假设就是某种“合理选择”(reasonable selection)的结果。
然而“合理”意味着原初状态及其种种假设条件在理论逻辑上还不是最原初的,更原初的东西是所谓“理”(reason or rationale),如下述的“平等”观念、“正义信念”等。(4)罗尔斯说:首先,“假定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的平等是合理的”[17]。这就是说,“平等”的观念是比“原初状态”更为原初的东西。但罗尔斯本人并不认为“平等”是一条正义原则。平等乃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观。关于平等,下文还将更为详尽地加以讨论。(5)在罗尔斯那里,除“平等”假设外,原初状态还须假定其它一些假设条件,诸如“作为道德主体、有一种他们自己的善的观念和正义感能力”、“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具有必要的理解和实行所采取的任何原则的能力”等等,这些假设都是值得商榷的,这里姑且放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证明一种对原初状态的特殊描述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这就是看被选择的原则是否适合我们所考虑的正义信念”。[18] 这等于说,正义原则是由正义信念奠基的。罗尔斯说,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这种正义信念是以“正义感”和“直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19] 这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其一,这种“正义感”和“直觉”,按照我们也赞同的罗尔斯本人的看法,也并不是正义原则;其二,罗尔斯并不能说明这种“正义感”和“直觉”的来源,而这正是中国正义论曾加以揭示的。[20]
第三、最后,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蕴涵在两个所谓“正义原则”及其“规则”中的那些基本观念视为真正意义的正义原则(尽管罗尔斯本人并不这样看)?这些观念包括:自由、平等。
在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或“仁爱”、“爱”是被罗尔斯排除在正义理论之外的。[21] 尽管他在谈到差别原则时为博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辩护,[22] 然而在他看来,对于仁爱来说,毕竟“困难在于对几个人的爱,一旦这些人的要求相冲突,这种爱就陷入了困境”;“只要仁爱在作为爱的对象的许多人中间自相矛盾,仁爱就会茫然不知所措”。[23] 这一点是与中国正义论的看法截然相反的,在中国正义论看来:一方面,正因为爱(严格说来只是仁爱中的差等之爱一面)导致了矛盾、利益冲突,这才需要确立起正义原则来指导社会规范的建构,从而调节这种矛盾冲突;而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仁爱(仁爱中的一体之仁一面)才确立了正当性原则、从而保证了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义。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其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这个道理,荀子是讲得最透彻的。然而这个道理是罗尔斯所不明白的,所以,他的思路是:“在原初状态中,各方是互相冷淡而非同情的”;正是“在无知之幕条件下的互相冷淡引出了两个正义原则”。[24]
我们再来看看罗尔斯的“平等”与“自由”的观念。
我们发现,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建构中,似乎“平等”、“自由”,或者说“平等的自由”[25],才真正具有某种基本原则的地位:不仅“进一步的契约”、而且“原初契约”(即罗尔斯所谓“正义的两个原则”),亦即所有社会规范的设计及其制度的安排,都必须符合这种“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此而论,在中国正义论中,当我们从正义原则推出现代性的社会规范时,我们是承认这一“原则”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认为“自由”、“平等”或者“平等的自由”就是真正的正义原则。这不仅是因为“自由”、“平等”的观念其实仅仅是现代性观念当中的一些价值观念(详下),而且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罗尔斯本人并不把“自由”、“平等”或者“平等的自由”视为正义原则,而是视为引出其“正义原则”的前提条件,甚至是其前提条件之前提条件、即引出“原初状态”的条件。不仅如此,他甚至同时又有一种与此相矛盾的看法,例如:“我在大多数地方将联系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来讨论自由。在这些情形中,自由是制度的某种结构,是规定种种权利和义务的某种公开的规范体系。”[26]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乃是思想的混乱:究竟是“平等的自由”决定着某种社会规范体系及其制度,还是这种制度规范决定着“平等的自由”?
此外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来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罗尔斯正义论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在排除社会共同体中任何一方的价值观成见的条件下得出正义原则,或者说是探索一个社会共同体如何在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各方之间达成一致的正义原则,如此说来,这种正义原则就不能依赖于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自由”、“平等”恰恰是若干不同价值观之中的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各方都一致的价值观,而罗尔斯的正义论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罗尔斯假定在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下的各方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种价值观,这是一种靠不住的想当然。
三、正义原则的普适性:不仅仅适用于现代社会
罗尔斯的整个正义论,都是基于上述“自由”、“平等”观念的。即便如上文所谈到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可能是更切合于“(正义)原则”概念的,我们还需要指出:“自由”、“平等”观念其实都是一些现代性观念,这些观念其实是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东西。因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某种现代生存方式,而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universality)[27],亦即不能解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制度何以可能。作为由现代生存方式所给出的现代人,我们也是主张自由和平等的;然而,假如我们要建构某种一般正义论(general theory of justice),这种正义论及其正义原则就应当是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域的。
因此,罗尔斯基于这种“自由”、“平等”观念而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不仅如上文已说明的那样,是把规范误认为原则了,而且其实是把现代性的某些特定的基本社会规范误认为是一般的正义原则了。于是,他说:
我设想一旦各方在原初状态中采用正义原则之后,他们就倾向于召开一个立宪会议。在这里,他们将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抉择一部宪法,可以说,他们是这种会议的代表。他们服从已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约束,将为了政府的立宪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设计出一种制度。[28]
在这个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仿佛就是当年美国的制宪会议的情景。
显然,建立在这种现代性观念基础上的正义论,至多只能叫做“现代社会正义论”,而非一般正义论,后者可以解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按照理论的逻辑,“现代社会正义论”应该是一般正义论的一种演绎。然而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除西方现代制度外,甚至除美国的基本制度外,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制度都是不正义的。如此说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正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恶的历史。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结论。
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一般正义论及其正义原则,是那种能够解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制度何以可能的理论。中国正义论就是这样一种正义论,它不仅通过正当性原则来要求制度规范的建构出于仁爱(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29])的动机,而且通过适宜性原则来充分考虑制度规范的建构在不同生活方式中的效果。这样一来,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可以由此而加以评判、得以解释。
四、正义的含义:不仅仅是公平问题
正义论的核心当然是正义问题。然而,“正义”这个概念的外延究竟如何?罗尔斯对“正义”概念的基本规定是:“正义”是指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30]。他说:“一个人可以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公平的正当设想为一种对正义概念和正当概念的定义或阐释。”[31] 于是,我们可以追问:正义仅仅意味着公平吗?这是关乎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正义概念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不妨仿照罗尔斯的一种惯用的说法:这里直觉的观念是:公平并不等于正义,正义也不等于公平。然而尽管罗尔斯自己也说“(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各种正义概念和公平是同一的”[32],但是无论如何,毕竟在罗尔斯那里“作为公平的正义”意味着“正义”(justice)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公平”(fairness)概念。有鉴于此,罗尔斯的书名《正义论》应该被更确切地叫做“公平论”(A Theory of Fairness)而不是“正义论”。
固然,罗尔斯完全正确地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3] 然而一旦把这句话里的“正义”置换成“公平”,那就很成问题了:无论如何,绝不能说“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更不能说公平是一切社会规范的首要价值。所谓价值,从正面意义讲,泛指所有一切可以评价为“好的”东西,亦即罗尔斯所说的“善”(good)。然而显然,一个社会制度所追求的最高的“好”或“善”绝不是“公平”。
有意思的是,罗尔斯有时却又自相矛盾地把“公平”限制在“正义”之下的层级,他说:
我们就可以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与两个正义原则的民主解释如此联系起来: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与公平机会的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原则的平等观念;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34]
在这段重要论述中,比起“正义”来,“公平”显然是一个次级概念,因而远远不能涵摄全部正义原则,即不涉及差别原则。在罗尔斯那里,“公平”主要是指的机会方面的平等。既然如此,“正义”就并不是什么“作为公平的正义”了,“正义论”也远不仅仅是“公平论”。
罗尔斯有时对“公平”还有另外一种说明:
“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名称的性质:它示意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各种正义概念和公平是同一的,正像“作为隐喻的诗”并不意味着诗的概念与隐喻是同一的一样。[35]
在这种意义上,“公平”不仅不等同于“正义”概念,而且与“正义”概念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而是正义原则的前提,略相当于“平等”这个现代概念。
以上表明,罗尔斯在“正义”概念、“公平”概念及其关系的问题上是不无混乱的。确实,“正义”是一个涵义很丰富的概念,其内涵远不是“公平”可以概括的。在中国正义论看来,“正义”至少包含以下语义:正当(公正、公平);适宜(时宜、地宜)。[36]
五、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一般正义论:正义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特别加以澄清的:诸如所谓“正义”、“正当”这样的词语,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中使用:一种是指的行为的正当,亦即是指的某种行为符合某种既有的制度规范,我们可称之为“行为正义”(behavior justice),这显然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另一种则是指的上述制度规范本身的正当,我们可称之为“制度正义”(institution justice),这才真正是正义论的范畴。不论是对于正义论、还是对于伦理学来说,这个区分都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并非任何制度规范都是“应当”遵守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法”本身就属于社会规范),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正义。例如,我们今天不必、也不应当遵守奴隶制度的社会规范。孔子说过:“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解释:所谓“乡原”就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我们没有遵从末俗、服从暴政、遵守恶法的义务。我们是首先根据正义原则来判定某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正义,然后才按照这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正当,例如该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或是不是合法的。罗尔斯说得对:
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里,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37]
以上分析实际上逼显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正义论是比伦理学更具优先性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对于传统观念来说就是颠覆性的。迄今为止,通常认为,正义论应该建立在某种伦理学的基础之上。我们的上述分析表明:正义论即便不是优先于任何伦理学的,至少也是优先于规范伦理学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是狭义的,是指那种仅仅列出社会规范、而并不追究这些社会规范的背后根据的伦理学。
当然,规范伦理学也可以追寻社会规范赖以成立的根据。这又可以分为两类情况:有一种常见的传统规范伦理学,它们追溯社会规范的根据,但是这种根据却是形而上学的——神学形而上学的、或者哲学形而上学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亦即或者并未涉及正义原则(义),或者简单地断定凡是出自“形而上者”(上帝或者理念之类)的就是正义的。
或许,我们也可以设想另外一种规范伦理学,它是追问社会规范赖以建立的正义原则的。这就涉及到近些年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制度伦理学”问题了。对于“制度伦理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ethics of institution”,即关于制度的伦理学;另一种是“institutional ehtics”,即是从制度角度来研究的伦理学。它们显然都是伦理学的分支。但是,上文已经谈过,一般来说,所谓“制度”也就是社会规范的制度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制度伦理学”也就是某种“规范伦理学”。但也可以更确切地说,一般正义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学,可称之为“基础伦理学”(fundamental ethics)。中国正义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伦理学。
总之,一般正义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尚待澄清的问题。
[①] 关于“可对应性”与“非等同性”,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第4-8页。
[②]《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③]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④] 黄玉顺:《“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⑤] 罗尔斯:《正义论》,第16-17页。
[⑥]《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⑦] 罗尔斯:《正义论》,第12页。
[⑧] 参见黄玉顺:《“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一、伦理规范与伦理原则,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⑨] 黄玉顺:《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 第5期。
[⑩] 罗尔斯:《正义论》,第302页。
[11] 罗尔斯:《正义论》,第302-303页。
[12] 罗尔斯:《正义论》,第62页。
[13] 罗尔斯:《正义论》,第258、157、158页。
[14] 罗尔斯:《正义论》,第173-174页。
[15] 罗尔斯:《正义论》,第17、21、18页。
[16] 罗尔斯:《正义论》,第18、17页。
[17] 罗尔斯:《正义论》,第18页。
[18] 罗尔斯:《正义论》,第19页。
[19] 罗尔斯:《正义论》,第19页。
[20] 黄玉顺:《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 第5期。
[21]“博爱”本是中国儒家的一个观念,如韩愈《原道》所讲的“博爱之谓仁”。现代用汉语的“博爱”去翻译西方的“fraternity”(兄弟情谊),这是并不确切的。
[22] 罗尔斯:《正义论》,第105-106页。
[23] 罗尔斯:《正义论》,第185页。
[24] 罗尔斯:《正义论》,第185页。
[25] 罗尔斯:《正义论》,第201页。
[26] 罗尔斯:《正义论》,第200页。
[27] 今天,人们有时把“universal”或“global”译为“普世的”,有时又把它译为“普适的”,这实际上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我倾向于作出这样一种区分:用“普世的”(global)来指在特定时代生活方式下的普遍性,例如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民主”这种价值观应该是普世的;而用“普适的”(universal)来指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这才是一般正义论所要追寻的东西,而“民主”这样的价值观(例如在柏拉图看来)就不是普适的。
[28] 罗尔斯:《正义论》,第194页。
[29] 有的学者将儒家的“仁爱”仅仅理解为差等之爱,这是极为偏颇的。儒家的仁爱不仅承认差等之爱的生活实情,而且特别倡导超越这种差等之爱的一体之仁,这是中国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30] 罗尔斯:《正义论》,第17页。
[31] 罗尔斯:《正义论》,第111页。
[32] 罗尔斯:《正义论》,第12-13页。
[33] 罗尔斯:《正义论》,第3页。
[34] 罗尔斯:《正义论》,第106页。
[35] 罗尔斯:《正义论》,第12-13页。
[36]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二、汉语“义”的语义,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37] 罗尔斯:《正义论》,第110页。